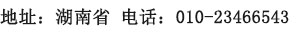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专业性文学出版机构,我社与茅盾先生渊源很深。我社第一任社长冯雪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曾借住在茅盾先生家里。作为左翼文艺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共同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以来革命文艺持续健康发展。
年我社成立后,为了继承和弘扬“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组织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的全集和文集,年《茅盾文集》第1卷由我社出版,至年十卷本《茅盾文集》隆重推出。紧接着,茅盾先生的代表作《子夜》等经典作品,也由我社印行,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茅盾先生晚年的重要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也是在我社《新文学史料》杂志年创刊号上发表,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年,我社历时22年推出了43卷《茅盾全集》,是当时规模最大、收集最全的茅盾总集,是研究茅盾著作的十分完备的版本。未来,我们还将推出《茅盾全集》修订版,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与我社《鲁迅全集》比肩的《茅盾全集》权威定本。
茅盾先生是一代文学巨匠,是与鲁迅齐名的中国现代文坛大师级作家,创作的《蚀》三部曲、《子夜》《腐蚀》《林家铺子》《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小说泽被后世;他是著名的编辑家,他主持的《小说月报》为新文学的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文字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让人难以忘怀的奉献与努力;他临终前,捐献自己的25万元稿费设立的“茅盾文学奖”,迄今仍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之一。
今夜,“茅盾文学奖之夜”颁奖活动将在茅盾先生故里桐乡举办。今夜,他的名字将被无数人提及,他的名字将久久回荡。在这一重要时刻,让我们走近这位“中国新文学的老长年和老保姆”,记住他为文坛所作出的艰辛努力,以及他身后留下的丰厚精神遗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和以前一样,把培养、鼓励青年作家,作为自己的分内工作,满腔热情地鼓励支持作家们的创作。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评论过作家数以百计,扶持过的作家也不在少数,这是茅盾在新中国文化部长的位置上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之一。以前的不说,光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当中,就有不少是被茅盾提携评论过的,如王安友、峻青、林斤澜、杜鹏程、李准、王愿坚、丁仁堂、茹志鹃、管桦、王汶石、权宽浮、肖木以及申蔚、勤耕、绿岗、乐天、穆寿昌、田军、麦云、张弓、范乃坤、车如平、傅绍棠、吴华夺、李魂、欧琳、刘克、杨旭、邓洪、费礼文、胡万春、万国儒、申跃中、韩文洲、玛拉沁夫、冯骥才等,许许多多的作家,或多或少得到茅盾的关心和帮助,鼓励和评论。所以在新中国的文坛上,茅盾有“文坛保姆”之称。尽管这么多作家当中,不少的作家是昙花一现,现在的人们早已忘记其中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但是对当年新中国文坛来说,依然是无法忽略的。
有一些作家因为茅盾的评论和提携,改变了人生命运,从而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作家茹志鹃,茅盾在评论《百合花》之前并不认识茹志鹃,在茅盾认识的人中,也没有人告诉茅盾,茹志鹃是谁。茅盾只是读了年3月《延河》文艺杂志上的小说《百合花》后,才知道有个作家叫茹志鹃。茅盾也只是觉得人才难得,这篇小说风格清新俊逸,才写评论,才充分肯定这篇小说的。据说,当时茅盾读到《延河》文艺杂志年3月号上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时,眼睛一亮,有着丰富创作经验和审美经验的文化部长茅盾,像在沙漠里突然发现了绿洲,非常欣喜!当他在5月12日读完茹志鹃的《百合花》后,十分欣喜地说:《百合花》“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用相当的篇幅分析肯定和高度赞扬《百合花》,认为《百合花》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最富于节奏感的”。连用两个“最”字来肯定《百合花》的结构和节奏感!至于人物形象,茅盾也给予高度评价:《百合花》里的“人物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越近越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同时,还以他丰富的审美经验,充分肯定茹志鹃《百合花》“清新、俊逸”的创作风格。高度肯定她的创作手法,称赞《百合花》中“善于用前后呼应的手法布置作品地方细节描写,其效果是通篇一气贯串,首尾灵活”。认为,茹志鹃写《百合花》时在“展开故事”和“塑造人物”两个方面结合得非常好,“尽量让读者通过故事发展的细节描写获得人物的印象;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的自然和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他就嵌在我的脑子里,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年5、6月间,茅盾集中时间将全国年、年发表的上百篇小说读了一遍,以札记的形式写下了几万字的《读书杂记》,其中,茹志鹃又是十分幸运,她的《春暖时节》《澄河边上》《如愿》《三走严庄》《阿舒》《同志之间》六篇短篇小说进入文学巨匠茅盾的视野,茅盾对茹志鹃的这六篇小说每篇都有精辟的点评。茅盾读过《春暖时节》,认为她“写静兰(女主角)思想发展的过程很细致”。“特点在于细腻地刻画了女主角的思想发展而不借助于先使矛盾尖锐化,然后讲道理,说服、打通思想等等通常惯用的手法。”肯定茹志鹃突破公式化的写作痼疾,已经有了自己的清新的写作特色。对小说《澄河边上》,茅盾还充分肯定“《澄河边上》写自然环境、故事发展,都紧密相扣,前后呼应,既写戎马仓皇,也写宜人风物;全篇节奏有起有伏:而这一切只用了七千余字,笔墨之精炼即此可知”。对《如愿》,茅盾认为其中的主人公刻画得非常成功,出场时“有挺胸向前的气概”,所以在写作上有“爽朗凌厉”的感觉。对《三走严庄》,茅盾写了近千字的评论,认为“这篇小说的女主角是作者所写的女性中间最可爱也最可敬的一个”。以她清俊的笔墨“活画出一个娴静温柔但看得清、把得稳,时机到来时会破樊而出的一位青年妇女——收黎子”。而且这篇小说的结构是“整齐而又有变化”。而小说《阿舒》,茅盾认为作者用第一人称写法,显得“文笔轻俏”,但因又注重形象的细节描写,把主人公的“面目和思想写得十分鲜明而活泼”。
《同志之间》是茹志鹃年发表在3月号《上海文学》上的一篇小说,茅盾认为,这篇小说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巧妙地安排的生活小故事,既渲染了战胜行军的气氛,也刻画了这三个人物,并且描写了经常闹意见的这三个人实质上是极其相互爱护的”。所以,茅盾说:“从塑造人物这个角度看来”,茹志鹃“取材于解放战争的作品更胜于取材于‘大跃进’时期的作品。”因为一代文学大师茅盾的评论,已经蔫倒的百合花又焕发青春,让处在人生低谷的茹志鹃又振作起来,成为新中国的著名作家。
茅盾在读过各地文艺杂志上发表的大量作品之后,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丁仁堂的《嫩江风雪》、申蔚的《洼地青春》、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勤耕的《进山》、绿岗的《忆》、管桦的《暴风雨之夜》等短篇小说,给新中国的作家们巨大的鼓舞。王愿坚后来回忆说,当时他看到茅盾的评论惊呆了,“使我惊奇的是,文章分析得那么仔细,连我在构思时曾经打算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后来又把‘我’改成了另一个人物这样一点最初的意念都看出来了,指出来了。他对那样一篇不满二千字的小说,竟用了四五百字去谈论它,而且给了那么热情的称道和鼓励。我被深深地激动了”。玛拉沁夫的《花的草原》出版后,茅盾在公务之余认真阅读,并且写了意见。玛拉沁夫读到这篇文章时,“愧不自容地哭了”!这样的感情,在当年的许多作家心里都曾经有过。敖德斯尔是蒙古族作家,在他成长过程中,茅盾同样倾注极大的心血,当年茅盾在读到敖德斯尔的小说时,同样还不认识他,只是觉得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需要国家大力培养,需要精心呵护。所以当时茅盾写评论,肯定敖德斯尔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欢乐的除夕》,认为“整篇是有风趣的,这是别有风味地描写了新人新事,有地方色彩”。敖德斯尔后来回忆说,当时看到茅盾对他的小说的评论,感到:“这对我是个多么大的鼓舞,又是多么大的动力啊!”敖德斯尔还记得:“年冬天,先生读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遥远的戈壁》之后,全面分析了我的创作道路的时候写道:‘敖德斯尔于年开始业余写作,用蒙古文,最近二三年也用汉文写。……’当时我读到先生的这些文字,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
北京作家林斤澜,但是在年当初还没有出名时,他投给杂志的小说稿子一直被《人民文学》杂志社压着,杂志编辑部的编辑对林斤澜的写法吃不准,是否可以发表林斤澜的作品也有争议。于是他们向茅盾请教,茅盾看过林斤澜的近20篇作品稿子以后,建议《人民文学》杂志社召开座谈会,后来,根据茅盾的提议,《人民文学》杂志社召开了座谈会。在会上,茅盾给以林斤澜的写法给以充分肯定,认为“林斤澜有他自己的风格。这风格表现在练字、造句上,也表现在篇章的结构上”。从此,一个文坛新星冉冉升起,林斤澜成为北京新中国以后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之一。
直到茅盾晚年,对文学新人的培养依然不遗余力,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给出版社后,出版社吃不准,也是由茅盾给以肯定之后才出版的。出版以后,果然引起社会广泛好评。在五十年代的岁月里,作为文化部长、作家协会主席,政治运动当中,虽然对一些作家也有批评批判,尤其是青年作家,茅盾开始的支持肯定却是真诚的。当年北京的青年作家刘绍棠刚刚冒出来时,茅盾马上给以肯定鼓励。年9月,茅盾曾经说过:“中国地大物博,大有人才在,通县不出了个刘绍棠?他的《山楂村的歌声》,我看不见得比苏联那个差?”
节选自《茅盾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年9月出版
推荐阅读
全新史料披露还原历史真实四十余万文字三十余幅珍贵照片读懂一代文学巨匠的“为人生”与“不尽才”
#欢迎大家积极留言评论,我们将根据留言内容、